【深度】Vlog:等风口来

一位豆瓣网友说:如果你在B站搜索Vlog,看到的内容十有八九是有人拍自己早餐吃牛油果酸奶拌麦片。
尽管这话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也的确代表了当下年轻人对Vlog的一种直观感受:他们无法确切地给这个品类定义,但是当看到某些内容时,还是可以模糊地分辨出它到底是否Vlog族类。这种分辨通常经由某些关键元素确认:比如榨汁机、咖啡机、面包机、烤箱,比如阴天、雨天、窗帘、地毯、阳台和落地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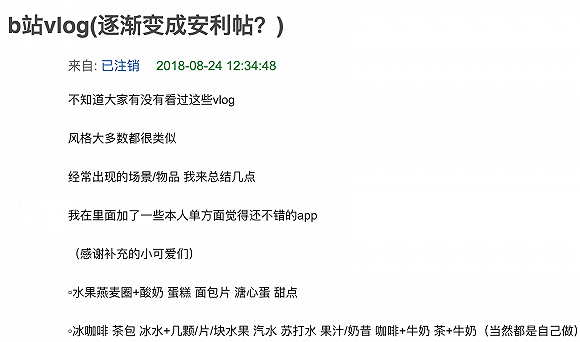
Vlog,全称是Video Blog或者Video weblog,中文一般译为视频博客。这个早先从YouTube上火起来的内容品类,经由各路网红博主们推广,再趁着欧阳娜娜的热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流量池。根据今日头条的数据,欧阳娜娜的12期Vlog在头条和西瓜视频上共获得超过7700万点击。
相比稍纵即逝的短视频,Vlog的信息浓度要高得多,这种浓度可能使我们感到快感刚刚好。它们通常不会超过半小时,低于更需要时间的长视频。根据QuestMobile的2018年互联网半年大报告,短视频用户总使用时长已经增加了3倍,在二级细分热门行业里占比达到8.8%。用户对于轻内容的需求已经逐渐明晰。
但Vlog的出现也唤起了我们某些迷思:它究竟只是一种记录渠道,还是一种新表达方式?它是一种媒介,还是说它的本身就是一种信息?
Vlog再造了一批新网红,也革新了我们对于短视频过去的种种认知,尽管我们还未见得足够理解它,但是这的确是它造物的季节。
站在时代的浪潮上,Vlog向我们扑面而来,我们认为有必要好好审视一下这个新生事物了。
不要充当三脚架
“如果一个奇观美景,你只是充当一个三脚架的身份,举起了你那个很昂贵的相机对着它,那无论最终获得多少关注,也是因为景色美而已,跟你无关。”
在解释一个Vlogger到底在干什么时,井越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井越其人,曾经是人人网网红,撰有《在阿姆斯特丹吃迷幻蘑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一文,行文诙谐而被大众所知。后来他做了《恶毒梁欢秀》的编剧,发现Vlog是一种以个体之力也可以表达喜剧的载体,从此专注于Vlog。做了快两年之后,他给自己的作品下了一个有点玄的定义:一种在当代国内sns上比较不同且难以复制的喜剧形式。

井越;图片来源微博
“我在Vlog添加的东西,最重要的并不是某个旅游目的地,而是喜剧元素。我会放一些即兴喜剧的东西进入视频,这时候无论我在家还是在旅游,其实最终呈现出的都是以我为核心的作品。”
比如井越在曼谷时留意到了餐厅里挂着的奇怪标语:不要担心,我们的所有店员都已经习惯了你的蠢问题,因此在用餐时就苦思如何提出蠢问题挑战店员。又比如,他把一些花絮单独做了一个“Not a vlog”的栏目,其中有和女朋友在当群演时捡假钱的片段和一只羊试图在啃饲养员的腰包。这些细节都离奇而富有趣味。

"Not a vlog"片段
作品里的另一个关键元素是“小箱”,这其实是一只灰色的玩偶小象,但在井越眼里,它是一个有独立灵魂的朋友。小箱有时候在猫身上蹦迪,有时则作为调节合照气氛的道具而存在。在井越和陈柏霖去年11月的一张合照里,小箱也出镜了,井越的配文是:小箱又局促了。事实上,真正害羞的那个人可能是井越——因为在此之前,一部分人觉得他长得像陈柏霖。

小箱

井越、小箱与陈柏霖
这些趣味一一体现在井越的作品里,就像他在某个短片里的提示字幕一样充满了漫不经心:拍摄前他们做的准备,其实是照镜子和撕嘴唇皮。
“有很多‘好笑’或其他感悟都藏在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里,我去帮大家把它们找出来。”用井越自己的话说,他是在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去接近“平常”。
和井越不一样,史里芬在竭力找出来的则更像是一种魔幻日常。这位自称为“华北观察者”的北方人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天津生活了四年,对华北有着一种独特认知。
史里芬关注的核心是在常人眼里几乎隐形的河北,因为他意外地发现,这个特大城市带几乎从不产出热搜。
“保定有1300万人口,邯郸有1200万人口,加起来比上海还要多。这么大的流量池,如果它还没有被引爆的话一定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版权保护: 本文由 沃派博客-沃派网 编辑,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bdice.cn/html/28086.html



